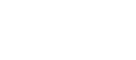“知识”是石器时代的概念,现代人类需要彻底转换思路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前一段时间很火的一片文章的标题有点耸人听闻:《揭秘东南亚“杀猪盘”:中国剩男剩女的人生屠宰场》。所谓杀猪盘,是指一群渴望爱情的男女在网上邂逅了几乎完美的恋爱对象后,在对方的蛊惑下参与网络赌博,当全部积蓄和借款全部充进博彩账户后,“恋人”和钱财一起消失的骗局。在那些“恋人”眼里,他们只不过是用所谓“爱情”圈养的“猪”,养肥了自然要“杀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杀猪盘?伦敦大学学国王学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哲学教授,曾任亚里士多德学会及心灵学会会长,《哲学工具》与《得分》等书作者的David Papineau认为,这是因为与间接的统计证据相比,我们更愿意相信直接接触到的“知识”而不是间接的统计证据。他认为知识根本不是真理的试金石,而是一个石器时代的概念,会对我们应对现代世界的能力造成损害。原文标题是:Knowledge is crude。
我反对知识。不要搞错:我跟身边人一样喜欢事实。我不是假新闻的朋友。我想要事实而不是谎言。我反对的是特定的知识,不是真正的信念。知识对我们的要求比真正的信念要多,这不值得。事实上,知识的概念是石器时代思维方式的残留,它的概念要比它的用处活得更久。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会过得好很多。
哲学家喜欢展示知识是如何超越了真正的信念的。为了看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妨想象一下在没有很好的理由的情况下,你确信一匹叫Meadowlark的马明天将在Ascot赢下比赛。然后假设它确实轻松获胜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说你具备了它会获胜的知识,这只是因为你的信念被证明是对的。
除了真正的信念以外知识还需要什么?一个自然的想法是你的信念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撑。不能仅仅是你正好蒙对了。但这个似乎也还不够。想象一下一位朋友给你买了张彩票当作礼物。你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你相信自己不会中奖,你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中奖的概率是百万份之一。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结果证明它确实没有中。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说你具备了这张票毫无价值的知识。你的信念可能非常合理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要想把它说成是知识仍然似乎太牵强附会。
对于那些从事认识论(“知识论”)工作的哲学家来说,他们的圣杯是要明确知识的本质并解释为什么知识的本质很重要。但是,尽管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文章专门来讨论这个话题,但哲学家们还是想不出一个好故事。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剥错了树皮。知识的概念实际上并没有挑出任何重要的东西来。这是我们从史前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粗糙的概念,在我们跟现代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屡屡会从中作梗。
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我们的史前祖先无法掌握像信仰这种复杂的代表性概念。相反,他们对那些接触事实的思想家和那些不接触事实的思想家进行了粗略的区分。这种初步的思维方式依赖于知识的概念。但我们再也不需要这种概念了。真正的信念的现代概念要微妙得多、灵活得多。但是,陈旧的知识概念不知为何仍控制着我们,就像我们无法摆脱自身体系的老情人。它在很多方面都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真的需要把知识忘掉。
等会儿我会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但首先让我讲讲它造成的伤害。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跟法律里面对统计论据的处理有关。法庭对此陷入了可怕的纠结,这一切都是因为知识的概念。
想象一下100名囚犯正在监狱的院子里锻炼,突然有99名囚犯袭击了守卫,执行一项第100名囚犯不参与的计划。现在其中一名囚犯正在受审。警方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证据。那么这个人有罪的可能性是99%,无辜的概率为1%。法院应该定罪吗?每个人的第一反应是——当然不能。法院没有信息可以排除被告就是那名无辜的囚犯。你不能仅依靠统计证据对某人进行定罪。
发生在监狱院子的骚乱是一个虚构的例子。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许多真实的法庭案件中,而且当它出现时,法律往往遵循平常的直觉。纯粹的统计证据是不够的。在民事和刑事审判中,只有当证据与被告有关系时,被告才需要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将其置于可能有罪的一般分类当中。
这也许一目了然,但这条对统计证据的法律禁令令人费解。想想一个男人因为有目击者称自己看到他偷了一条项链而被定罪。幸运的是,如今法庭知道目击证据也有可能出错,所以他们会仔细核查以确保可靠。即便如此,只要目击者让怀疑显得不合理的话,法院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性——这似乎意味着类似95%之类确信度,只要能说服法官给这种确信度明确一个数字。
因此,我们往往能接受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来定罪,但从来都不能接受根据纯粹的统计证据来定罪。如果可靠性为95%的目击者比可靠性为99%的统计数据更可能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话,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还会这样。
对导致更多错误定罪的证据来源(如目击)的偏好,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
也许你认为这种比较只是表明了我们也应该提高目击者的水平。还有什么比对一个无辜的人定罪更糟糕的呢?但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偏信目击者而不是统计证据不是数字问题。哪怕有1000名或者10000名囚犯在监狱院子里,根据纯粹的统计证据来定罪仍然是错误的。对于统计证据来说,确信度再高也没有用。但是,没有人愿意把这样一个绝对的标准强加到目击者和其他更直接的证据身上。因为这意味着永远也无法定罪。
鉴于我们能接受其他类型证据一定的错误率,为什么我们又对统计证据避之不及呢?这是目前法律理论家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取得过太大的进展。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想法来自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哲学同事Clayton Littlejohn,他的想法把我们带回到了知识这个主题。
Littlejohn的想法是,除非犯罪是已知的,否则我们就不想定罪。如果我们相信监狱的被告是有罪的,那么100次里面我们会正确99次。但在我们对那99个案件的真正信念没有一个相当于知识——我们的正确只是巧合。相比之下,当目击者真正看到犯罪时,她就会知道这一点,当她在法庭上诚实地报告这一点时,她的听众也会了解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无法知道5%左右的情况下目击者证词在某种程度上会误入歧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其他那95%目击案例的知识。总之,虽然目击者给我们留下了5%的不了解犯罪事实的可能性,但统计证据却要差得多——它让我们的不知道变得确定。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顺利。这似乎是关于我们思维的一个貌似可信的解释。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只会把问题向后推。也许我们直觉上认为善良的目击者让我们了解了犯罪事实,而统计证据从来都没有提供真正的知识。但是,即便如此,为什么在法庭上权衡这种差异就是个好主意呢?毕竟,源自统计证据的真实信念源自从目击者的信念一样真实——且不说统计数据提供的事实要比目击者的可靠多了。仔细想想的话,你很难看出只有在犯罪已知的情况下才能定罪就是个好主意。如果法庭的目的是给犯罪定有罪让无辜者自由,同时避免相反的结果出现,那么偏好导致更多错误定罪的证据来源(如目击者)的逻辑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这其中必定存在一些逻辑,只是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可是尽管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们还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个。要我说这是因为这里面根本没有逻辑可言。事实上,我们更偏爱目击者而不是统计证据只不过是我们史前对知识粗糙的考虑的反映。这种偏见阻碍了我们给犯罪定罪让无辜者自由的事业,并且没有带来任何回报——要我说,这就是对知识的关切如何把我们的生活搞砸了的一个缩影。
要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跟统计证据的关系会搞得一团糟,我们需要回到知识这个概念的进化起源。许多动物都可以区分谁对某些事实是否熟悉。比方说,低地黑猩猩可以分辨雄性领袖是否能看到食物的诱人部分,如果能看到的话它们会去抓。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它们会依赖于视线:雄性领袖是否有清晰的视野,还是说有什么东西挡住它的道了?一般而言,动物对是否有东西挡住它们获取某些事实的去路很敏感。
我们可以将这种基本的分辨能力看作是为知识的概念提供一个基础。具有这种能力的动物可以将对象划分为知道某些事实的主体(agent)和不知道某些事实的主体。但这还没有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相信的概念,也就是在内心对真假做出判断。不过,随着人的慢慢长大,他们就能够具备这种更加微妙的理解。他们会慢慢明白,在不知道的人当中,把那些有着错误的信念的人跟只是不知道的人区分开是值得的。比方说,他们开始意识到,在那些不知道某块岩石背后有什么的人中,有些人可能会主动选择去相信那里有香蕉,哪怕其实并没有。具有错误信念的主体不仅不熟悉状况,而且还会主动去歪曲这种状况。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进步,因为伪信徒可以表现得像个知者而不是无知者。一个饥饿的主体错误地认为岩石后面有香蕉,你可以预料到他会走到岩石后面,就像知道这一点的主体一样。由于他们都相信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把伪信徒与相应的知者混为一谈,我们这些世故的人类预测行为的能力就变得好很多了。(当然,伪信徒实际上不会找到香蕉。通常只有真信徒才能得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进化人类学家还没法确定我们的进化祖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给简单的知识概念加入了更灵活的真假信念的。对人类儿童和其他动物的形成性和比较性证据不够明确。过去几年已经出现的一些证据表明,甚至某些类人猿也初步掌握了错误信念。但不管怎么说,进化的故事始于对知道和不知道的简单区分,以及更为空想一点的信念是随后出现的,对此大家似乎没什么疑问。
一旦信念的概念出现,旧的知识概念就变得多余了。我们现代的思想家可以区分三种主体:
信念符合事实的人;
信念歪曲事实的人;以及
没有意见的人;
我们还可以相应地预测他们的行为。此外,我们能领会真信念的实际优势,从而努力确保我们自己的信念是真的。上述任何思想类型都不需要古老的知识概念。
但不幸的是,旧的观念仍然牢牢地控制住我们。不妨再想想统计证据。我们也许认为受审的囚犯是有罪的。鉴于统计证据非常有力,极有可能这种信念是正确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根据我们的信念来采取行动。我们不会把信念归类为知识,所以觉得这是不牢靠的,不会认为我们跟事实有着适当的联系。
对知识的偏爱导致我们以违背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
实际上,我们被一种返祖的思维方式所左右。我们渴望从事实到思想有一条清晰和直接的因果路径,就好像香蕉与猴王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阻隔一样。目击者及其证词符合这种模式,但统计证据却不符合。统计证据太过间接了。我们现在可能会在理性的层面赏识迂回的统计推理能可靠地引导我们通往真信念。但不知何故,我们并不认为这跟真实的东西等同。对于它,我们缺乏那种对事实坚定信心。
这种对知识的偏好根深蒂固。我本人一开始也有这样的直观感受,即仅靠是100名囚犯之一这个证据就将被告定罪是错误的。我总会止不住去想,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被告是有罪的。
尽管如此,这种直觉还是不能经受住考验。没人会怀疑惩罚无辜的人是件可怕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准备好去接受一定最低程度的错误定罪的风险,否则的话我们最终会谁都惩罚不了。这个程度多少合适我们可以进行辩论。我不是宣扬法治的狂热分子。但我希望它可以低于法官似乎能接受的5%。尽管如此,无论正确的程度如何,仅仅因为我们认为目击者会赋予我们犯罪的“知识”而将目击者(的错误率)设定为低于统计证据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最终只会基于目击证人的证词上给太多的无辜者定罪,或者在当证据是统计性的时候释放太多有罪的当事人,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的直觉可能根深蒂固,但它们妨碍了我们达成目标。
法律回避统计证据突出显示出知识概念所造成的扭曲。但这个问题是普遍问题。相对于间接的推理,我们一刀切地更加信任直接知识的推测来源。而且,就像在法庭上一样,这不仅没有帮助而且还会给我们造成伤害。对知识的偏爱导致我们以违背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
再以买彩票为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以非常不合适的价格买下来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不会中,我们却对自己说一定会中的,尽管统计数据断然否定如此。然而,一旦我们有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在报纸上看到我们蒙中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时,我们很快就会改变主意,。哦,好吧,我们告诉自己,现在我们知道自己输了,于是把彩票扔进了垃圾桶。但是,如果报纸不可靠误报那两个错误的数字的话,那么拿到中奖彩票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对直接证据的嗜好掩盖了这一点。我在想有多少中奖彩票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弃领的。
一旦我们开始往这方面想,例子马上成倍增加了。一般而言,我们见过的人是值得信赖的。其实随便把我们的钱包交给某个陌生人一般都很安全。但是我们却非常不情愿这样做。对陌生人通常不会一有机会就拿着我们的钱包溜走的认知并没有根据。另一方面,直接接触很快就可以让事情看起来不同。我们在公交车站跟旁边那个很友好的家伙交谈,然后确定他是诚实人。但事实上,这种友好是可信赖的糟糕指征,但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东西了。一代又一代的骗子已经从这种对直接证据的非理性偏好中赚得盆满钵满(译者注:杀猪盘)。
诸如此类。我们总是偏爱较弱的直接证据而不是很好的统计数据。我们的邻居推荐自己的洗衣机,这会让我们对该品牌的可靠性比看某本杂志仔细研究过的统计数据有信心得多。朋友遭遇不幸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保险,即便保险的精算数据表明其实风险很小。一次又一次地,我们总是更愿意基于与迂腐刻板的直接原因知识相符的信息来采取行动,而不是依据好的统计数据。但这些都是糟糕想法。
在不顾一切想要找出一些关于知识概念的好用例时 ,哲学家们有时会说 “知识为断言提供了规范”。他们想的是你不能只是说出你的感受。首先,你不应该撒谎。其次你也不应该仅仅因为自己希望是真的而随便说出自己的愿望想法。你的断言要有支撑。哲学家的建议是,你需要的这种支撑就是知识。不知道的就不应该说出来。
好吧,这也许的确是我们的日常。如果目击者告诉了我们,我们会认为说“她偷了一条项链”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接着就会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唯一的证据是统计性证据的话,即使这极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断言“他攻击了守卫”,因为这些证据并不能提供知识。
这是我们目前的做法,要我说我们最好不要这么干。如果说断言的目的是传递有用信息的话,为什么要把它局限为知识呢?为什么只报告对我们产生盖然影响的事实,而排除掉我们有信心的其他事实?前面我已经展示了我们对知识的偏好其实扭曲了我们对行动的选择。在沟通中偏好知识只会传播这种瘟疫。其他人也将被引导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
我们已经核实消息提供者断言的精确性
所以我要对断言的知识规范表示藐视。这并不意味着怎么都行。除非你有理由确信,否则仍不应说“他攻击了守卫”。但强有力的统计证据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谁会关心直观上它不能提供知识呢?当然,有时你会不走运正好在有罪人群中碰见那那位无辜的囚犯。但是,当我们发布不确定的目击者证词以及其他不可靠的假定知识时,这种危险已经与前者所传播的虚假信息相抵了。
藐视断言的知识规范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的激进。我要说的是,在正确很重要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已经超越了任何粗糙的知识规范。不妨设想一场竞争激烈的酒吧问答游戏。团队成员会提交相互抵触的答案,而队长的工作是找出最有可能正确的答案。“你知道吗?”这个工具太粗糙了。明智的队长会设法找出这些建议的确切来源——你是靠猜的,还是最近看到过?或者通过一般原则推断出来的?
这同样适用于其他真相至关重要的情况。当我们依据某些消息提供者的观点选择在治疗方案、财务策略或旅行计划时,我们可不想把自己的信任完全依赖于对方是否“知道”上面。我们做得更好,去找出他们的建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支撑,并且判断是否要基于此来照做。
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语言都有一套“基于证据”的结构体系。在这些语言中,你不能仅仅下断言就行。你需要利用指向其出处的证据来标记所有断言。比如,加州的Eastern Pomo语就有动词后缀来指明你的信息来源是直接的的信息来源是直接看到的,其他感官感觉到的还是听说的或者推理的。相对于那些仅仅假设所有指示性说话方式均遵照知识的单一标准的体系来说,这样的体系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彻底改革语言。我们可以在没有证据性形式系统的情况下应付过去。如我所说,在严肃的场合下,我们已经靠其他手段取得了相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的话,我们会核实消息提供者断言的精确性。“知识”是一切断言的试金石这种简单的想法已经过时了。我们的信息提供者是否满足知识的直观要求根本不重要。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信念是否有可能是真的。
罗素曾经说过,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一种历史遗物,它所以能象君主政体那样残存着,在哲学中间代代相传,只是因为错误地以为它是无害的。” 罗素关于因果关系的说法可能是错的。但他的非难完全适用于知识的概念。这的确是一个过去时代的遗物,而且还是一个会造成明显伤害的遗物。我们应该摆脱它。
原文链接:https://aeon.co/essays/knowledge-is-a-stone-age-concept-were-better-off-without-it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