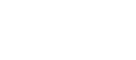互联网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技术能让我们看到一切吗?迈克尔·哈里斯在《缺失的终结》的开篇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部落聚集地,巴都利马的一个女孩,她的家里地上铺的是竹片,有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家里没有电,她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捡柴火。
赶上重要的日子,她的父亲会一大早赶到村里,把看电视要用的蓄电池充上电,然后她就能看电视节目。电视里,说着她完全不懂的美国话,但它又是那么的好看,充满了外国的气息,构成了她对外面的世界的全部憧憬。
渐渐地,她想要离开这个聚集地,离开马来西亚的过去。她想要更多,但却不知道“更多”是什么样子。18岁的时候,她离开家来到沙巴——一个只有2000人口的城市。在那里,她在肯德基打工,把薪水存了几个月,终于买了一部手机,那成了她的奢侈品。
她迫切地想进入现代世界的生活,慢慢地转到了更高级一些的餐厅去工作,虽然薪水还是一样,但这里会有游客来吃饭,她有了跟他们练习讲英语的机会。
在游客中,她认识了一位从加拿大来的同龄男生,他们开始约会。之后,男生回加拿大并承诺会在第二年回来。她不确定,但男生还是实现了她的诺言,最终把她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她实实在在地体验了“文化的冲击”,看到了之前在那台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画面。
几年后,她成为了加拿大人,带着笔记本电脑飘扬过海回马来西亚看她的母亲,把家里的电话线连上电脑,拨号连上了网络,兴高采烈地跟母亲讲什么是“谷歌”。
“这东西能让你知道一切。”她对母亲说。
“一切?”她母亲问道,满脸的疑惑。
“一切!你想看到什么?”
“我的投胎转世。”
历史上从没有哪两代人在认知方面如此不协调,因为从来没有一次技术变革来的如此迅速。人类接受一种新技术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收音机38年,电话20年,电视13年。
而新一轮的革命中,互联网是4年,Facebook3.6年,Twitter3年,iPad2年……
期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就像之前的几代人,也曾疯狂地迷恋电视机,但最终,电视机可以一直开着无人观看,正如之前被冷落的收音机,任凭它们低声细语。之后的数字原住民也必将被互联网淹没。
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了新的责任。比如,一部分编辑的宿命是,每天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来管理微博、Twitter、Facebook,进行互动。他们在管理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耗费着时间,盯着四方的电脑屏幕,创造着电子的虚无。
一个就职于杂志社、做编辑或专栏中作家,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内容创造者”了。因为这一行似乎已经被用“病入膏肓”来描述了。《大西洋月刊》描述了当前美国编辑在工作中的一类现象:在编辑会议上,领导总抱怨编辑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不够多,并想尝试开设新社交平台的账号。会议过后,编辑们回到自己的小隔间里,看着桌上那两台永不关机的电脑屏幕上,开着一个又一个窗口。
当你开始写一篇文章,刚敲了不到50个字,领导通过微信@你 ,你放下手头的事情去想怎么回复他。与此同时,同事给你发来一则某位艺人出轨翻转的微博新闻,你打开来看。那个活泼的实习生跑到你身边,问了一个问题,你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她。我们可能在数十分钟内,同时进行着几十种互动。这时,它们只是我们想要尽快处理关闭的窗口。
作家琳达·斯通在1998年就对我们当前的这种状况做了一个经典的描述:“持续局部注意力”。这是一种即兴的状态,现在我们每天都在被这种状态所主导。
如果说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件事,然后再开始做第二件事,那么“数字化生存”下的居民大多数都会疯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员盖瑞·斯莫(Gary Small)曾指出:“人们一旦习惯这种状态,就会在永不中断的网络中如鱼得水。他们的自我和自重将得到满足,而且不可阻挡。”
但技术本身并无道德可言。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说:“技术无所谓好与坏,也无所谓不好与不坏。”它们并无善恶之分,但对于通讯技术、社交网络总是注入了超越我们承受范围的热情,这造成了这种破坏自我的危险。
我们已经对网络活动有多么依赖和贪婪了?网络数字技术拉近整个世界,其速度令人发指。
2012年,人类每天用146种语言在Google上进行1万亿次的搜索;同时还发送1440亿封电子邮件。2013年,Facebook上,每天点在45亿次;Youtube上,每小时上传100小时视频;Instagram上,每秒上传637张图片。
过去十年,互联网使用率增加了566%。根据2017年最新的估算,全世界超过40%的人都在上网。我们在通讯设备和社交网络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其他的“可支配”时间中挤出来。
但可悲的是,我们根本做不到像《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一样,逃离城市,去享受远离尘嚣的“孤独”之旅。事实上,我们对周围人对自己手机,宛若襁褓中婴儿才有的那种专注与沉迷的状态习以为常。
的确如此,现在父母用电子设备来哄孩子,很多父母发现iPad既是一种兴奋剂也是一种镇静剂。当孩子开始哭闹不止时,细心的父母从装尿布的包里拿出iPad,他就立刻安静下来。商家甚至推出了一款名为iPotty的产品,其实就是在儿童马桶加上iPad,训练儿童如厕。
这也就难怪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看着地上的纸质杂志,用自己的大拇指捏住食指按住封面上的人物,并做拇指和食指分开的动作(苹果设备“放大”的手势指令)。试了几次之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想放大那张图片,最终孩子一脸困惑地看着家长,意思在说:这东西坏了。
所有婴儿都曾以为这个世界是触屏的吧,我们的下一代与设备在一起当然比跟同类的人在一起更加自如。密歇根大学集中了1979—2015年的72份研究美国大学生同理心程度的报告发现:如今的年轻人,更渴望减少关系、同理心更低、更加自恋;跟朋友交往发消息时,过多地依赖表情包及缩写字母的青年,更加冷漠,且缺乏同理心。
你用来接触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同样,在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被互联网侵犯之前,阅读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当印刷文字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我们的眼睛近距离盯着一本书看,高强度的眼力注视并非自然的动作,这改变了我们了解整体世界的态度。
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这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黎明、语言的规范以及视觉的主宰,并以损害我们多重感官的生活为代价。“眼睛高速运转,而声音慢慢降低。”我们主要通过眼睛获取信息,而少用其他感官。“信息即媒介”——麦克卢汉把这一切归咎于古登堡的发明。
如今,新一轮的爆炸将这种气氛已经飙至疯狂的地步,刺激我们的肾上腺释放大量肾上腺皮质醇和激素。使用电子设备的压力荷尔蒙会在短期内大量释放能量,使记忆力得到增强。但从长期来看,这会损害认知能力,导致忧郁症,并且改变脊椎海马体、杏仁核以及控制情绪和思想的脑前额叶外皮的神经元回路,甚至可能改变大脑的内部结构——所谓的“技术烧脑”。
《浅层思考》中描述了互联网如何对我们的可塑大脑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使大脑能够做“浅层”思考,而少做“深层”思考。如果我们在电脑面前浏览信息足够长时间,我们就能够学会如何更轻松地吸收更多地信息,如省略后半段不看,经常调整眼睛的焦距等,记忆完全外包给某种设备来管理。
互联网鼓励大家公之于众,但又同时将公布者远远隔离。许多人乐于“分享”生活的体验,却手忙脚乱地把生活赐予他们本身的快乐所抛弃,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人把自己的母亲的癌症诊断书发到朋友圈、把男朋友因艾滋病死亡的过程公之于众。接受一种“公开坦白的文化”让独处的宁静变得一文不值。
海德格尔有一对哲学概念,叫“闲聊”与“无聊”。闲聊的定义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个人,需要在与他人的简单的互动,或需要有外在的各种层出不穷的刺激当中,让他忘记他自己,或者说,让外力、让外人来占据他空空如也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他才感受到某种自在。
闲聊的底色是无聊。人的思维和情绪找不到互动、交流、交往的对象就会产生“无聊”。互联网让我们在不能忍受自己空空如也的时候,提供了用外在信息、用外力来占据自己的内心的闲聊出口。
但互联网式的闲聊并不是对于无聊的根本性的治愈,它只不过是类止痛片式的东西,在止疼片的药力消失之后,你又立即感受到疼痛。一个通过闲聊来缓解自己的不安的人,一旦切断了他与外界闲聊的通道,他就立即陷入到一种巨大的烦闷和焦躁当中。
周国平说:“世上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人们往往知道交往是能一种能力,却经常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它能够抑制住我们因久居城市而产生的好斗与神经质。
塞内加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都是他们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产生的。”然而,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并不如此,因为互联网生活是一种“躁动的闲散”。